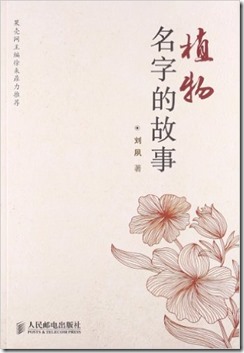还算有趣, 只是感觉有的内容太散了, 另外配图再丰富点就更好了.
一点点摘录:
巧合的是,在德国人中,阿道夫(Adolf)这个名字遭到了同样的冷遇。Adolf来自古德语Athalwolf一词,意思是“高贵的狼”。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阿道夫是德国男性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在植物分类学史上鼎鼎有名的阿道夫·恩格勒(Adolf Engler)就叫这个名字。然而,一切都因为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改变了——他创建了第三帝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把德国以至世界都带入了灾难之中。当1945年希特勒自杀、二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几个德国人愿意给男孩子取名阿道夫了。不过,这个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以变体“阿迪”(Adi)频繁出现在所有爱好体育的人们面前——德国著名的运动用品公司“阿迪达斯”(Adidas),就是以其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Adolf Dassler)的名字命名的。
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很多人对“四川”这个名字的词源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它是来自省内的四条大川。不过具体是哪四条大川,就说法不一了。有人说是“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也有人说是“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当然,这个误解由来已久,至少从清朝初年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开始了。“四川”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在于它是“川峡四路”的简称。所谓“川峡四路”,是北宋年间设置的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四“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的合称。
珙桐之美,不仅在于它那高大挺拔的身姿和翠绿欲滴的叶色,更在于它那奇特的花朵——两枚硕大洁白的“花瓣”(实际上是一种叫作“总苞”的叶状结构)中间,是一团紫色的“花心”(这是真正的花),远远看去,仿佛是树上停落的白鸽。正因为如此,珙桐在英文中就叫作dove tree(鸽子树)。
普尔热瓦尔斯基虽然是一个叫嚣“对付野蛮民族只有用钱和枪”的流氓,但是只要用他的名字对动植物命了名,这名字就再不能更改了。这就像1937年,一位昆虫学家谄媚地用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A. Hitler)的姓氏命名了一种甲虫(学名Anophthalmus hitleri),从此这种甲虫就再也摆脱不了希特勒之名了。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这种甲虫竟然成了新纳粹分子的钟爱之物,因为过度捕捉,竟然到了濒危的境地!
杜鹃又是一种特别容易和植物挂起钩来的鸟类。因为它是候鸟,如果在温带地区听到它的叫声,那就表明春天已至、万物复苏了。中国人之所以选取“布谷”二字来模仿大杜鹃的叫声,便是兼寓有播种的时节已到之意。在英国,被叫作cuckooflower(直译过来就是“杜鹃花”)的植物至少有10种,它们之间的唯一共性,便是都在人们听到杜鹃叫声的时候开花。
不过,中国人认知的“杜鹃花”和这些cuckooflower没有一点关系。杜鹃花是一大类植物,全部都是木本,以灌木居多,但也有些种也可以长成大树。最为人熟知的杜鹃花是广布于江南山区的映山红,在春末夏初盛开的时候,漫山遍野都笼罩在一片红光之下。据说这花曾经被杜鹃啼出的鲜血染过(“杜鹃啼血”是著名的中国传说),所以才会这么红,也因此才会叫作杜鹃花。杜鹃花属的学名则是Rhododendron,这个词由古希腊语词根rhodo-(意为“玫瑰”)和dendron(意为“树木”)构成,直译是“玫瑰之树”,也是在摹状它的花色。
究其词源,“胡同”一名可能是来自蒙古语qudduγ(按照今天的蒙古语发音,可以音译为“呼达格”),本义为“水井”(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胡同”是蒙古人统治中原百年之间,从蒙古语进入汉语的众多词汇之一。比“胡同”用得更广泛的另一个蒙古语借词是驿站的“站”,这是蒙古语jam(本义为“道路”)的音译。明朝初年,官府发文,全国改“站”为“驿”,以恢复汉语中的古雅名称,但是在老百姓的口语中还是一直用“站”。这样到了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之后,神州大地就只剩下火车站、地铁站、汽车站、公交站,而不再有“驿”了。反倒是在日本,“车站”这个词写成汉字还是“駅”(“驿”的繁体“驛”的日本简化字),读音也是从中古汉语演化而成的eki(えき)
薹”之名在古籍中早有记载。《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的前两句是“南山有台,北山有莱”,这里的“台”就是“薹”的本字。顺便说一句,曾有“历史学家”考证这首诗中的“有台”即“犹太”,以此论证《圣经》中所谓伊甸园本在中国。当我还在读历史学硕士时,这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专业笑话之一。另一个我最喜欢的专业笑话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中国商代人的后裔,商朝——也叫殷朝——被灭亡后,他们渡海逃亡,但不忘旧邦,见面时相互问候:“殷地安否?”因此被叫做“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