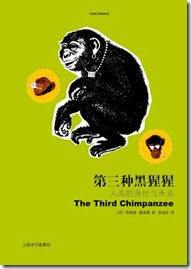直接贴一些摘录的内容吧:
传统分类学将所有大猿放在同一分类类目中(“猿科”),为人单独另立一个类目(“人科”),好像人与猿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自然鸿沟,对我们自居于“万物之灵”的“人本位”偏见,有推波助澜之功。现在呢?未来的分类学家也许可以用黑猩猩的眼光来处理高等灵长类的分类问题: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群,一群包括三种黑猩猩(人加上另外两种黑猩猩),另一群包括其他的猿(长臂猿与红毛猩猩与大猩猩)。
既然猴子、猩猩都有能力以声音传讯,为什么猿类没有朝这个方向演化,发展出它们自己的复杂语言? 答案似乎在涉及控制语音的解剖构造,包括喉咙、舌头,以及相关的控制语音的肌肉。就像一只瑞士表,它能够准确计时,是因为所有零件都是精心设计的,我们的发声道依赖许多构造与肌肉的精密配合。
所以我才认为促成大跃进的“东风”,是人类的“原始型”发声道变成了“现代型”发声道。从此人类能够更为精密地控制发声道,创造更多的语音。
我们很容易想象解剖学上的一个小变化导致说话的能力,从而在行为上产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要讨论这种社会组织如何塑造了男人与女人的身体。首先,就拿男人的身材比女人的高大一些来说吧。平均说来,男人比女人高8%,重20%。一位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看一眼我太太(173厘米)和我(178厘米),就会猜我们这个物种实行的是“‘轻微的’多偶制”。也许你会问:这可能吗?从两性的相对身材推测交配模式?
其实,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后宫”的大小与两性身材的差异成正比。也就是说,雄性娶老婆最多的物种,通常是雄性身材比雌性大很多的物种。
在“单偶制”的物种中,每个雄性都能赢得一个雌性;而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大多数雄性都输掉了赢得老婆的机会,只有少数雄性占据了支配地位,所有雌性关入“后宫”。因此,“后宫”越大,雄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这时身材就成为重要的制胜关键了,因为身材高大的雄性通常都会打赢。
对其他的动物,交媾是非常危险的奢侈品。当陷入忘我之际,动物必须燃烧珍贵的卡路里,忽略采集食物的机会,说不定天敌在一旁虎视眈眈,竞争地盘的对手也可能伺机下手。因此交媾是为了受孕才做的事,而花的时间越少越好。人类的性事就不一样了,以受孕来衡量的话,简直浪费时间与精力,是演化的失败。
理论1、2、4揭示的因素,我觉得今天仍在起作用,它们是同一个人类社会组织特征的不同面相。这个特征其实奇特得很,那就是:每一对男女,若希望自己的子女(基因)顺利长大成人,就必须长期合作,共同负起抚养的担子,但是,他们也必须与附近的其他夫妇合作,经营经济生活。每对夫妇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与其他的成年男女互动,但是规律的性生活,将夫妇的关系拉近,凸显了“夫妇”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差异,我想用不着多说。隐性排卵与随时可以性交的女性生理,加强了这个新的“性”功能——强化夫妇的关系(其他哺乳类的“性”功能只有一个——繁殖)。
社会生物学就像核子物理,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一样,会遭到滥用。虐待别人或谋杀,我们从来不缺借口,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演化逻辑也成为现成的借口。对人类性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讨论,可以当作男人监控女性身体的借口,或两性不平等现实的理论根据,就像传统体质人类学被用来支持白人奴役黑人、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两种恐惧不断地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异于主张那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那种行为。
在我看来,这两种恐惧都没有根据。就拿第一个来说吧,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可以研究,无论那些事物是令人厌恶或令人钦羡。研究谋杀犯的动机,就是为他们开脱吗?至于第二个恐惧,我们不只是演化结果的奴隶,甚至不仅是遗传特征的奴隶。
这些差异意味着:演化为两性写下了方程式,让女性花比较多的能量修补身体,男性花比较多能量斗争。换个方式说,就是修理男性划不来,不如修理女性。
农业对人类健康有害,至少有三组原因可以解释。首先,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种类繁多,蛋白质、维他命以及矿物质的含量适当,而农人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结果,农人得到的是廉价的热量,付出的代价是营养不良。今天,人类消耗的热量中,单单是三种高糖植物(小麦、稻谷、玉米)供应的,就超过50%。第二,由于农人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维生,要是庄稼歉收,饿死的风险比猎人大得多。爱尔兰大饥荒就是个例子。最后,今天大多数主要的人类传染病与寄生虫,要不是农业兴起,根本不会在人类社会中生根。那些人口杀手,只有在拥挤、营养不良与定居的社群中,才能长存。
农业兴起后,精英阶级变得更健康,但是许多人的健康恶化了。即使我们将进步史观抛开,不再相信“我们选择农业是因为务农对我们好”,一位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追问我们:如果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祸福相倚,那么我们怎么会陷溺于农业呢? 答案可以归结为一句格言:“强权就是公理。”农业能供养的人口,比狩猎多得多,至于平均说来是否每一张口都分配得到更多的粮食,是另一个问题。
同样地,应用扎哈维的理论解释雄性对雌性的仪式性表演,思路是这样的:任何一个雄性,要是背负着那么大的累赘装备,如孔雀的尾巴,或冒着生命危险大声唱情歌,居然还能活着,必然在其他方面有优异的基因。他已经证明了他必然特别优秀,不然无法逃脱猎食者,以及抵抗疾病。累赘越大,他受到的考验越严苛。选择这样的雄性,雌性就像中世纪的未婚少女考验她的武士追求者一样,她得看他们屠龙的本领。如果一位武士凭独臂就能屠龙,她立刻就知道他体内有优质基因。那位武士以独臂炫耀,其实是在炫耀自己的实力。
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文身不仅痛苦,也很危险,因为有感染之虞。因此文身的人事实上是在炫耀他们的力量——抵抗感染与忍受痛苦。
扎哈维理论也能用来解释人类滥用有毒化学品的行为,特别是在青春期与青年期——那是最可能开始吸毒的年龄——我们花费大量精力维护自己的地位。我认为我们与一些鸟类一样,有同样的无意识本能,鸟类会沉溺于危险的仪式性表演,在一万年前,我们以挑战狮子或部落敌人的形式,表演自己的勇武。今天我们以其他的方式表演,例如开快车,或服用危险的药物。
文明兴起的速率,各大洲不同,并不是少数天才造成的意外。也不是决定动物族群竞争结果的生物差异——例如有些族群跑得比较快,或食物消化得较有效率。也不是各族群平均发明能力的差异造成的结果——根本没有证据显示过有这样的差异。文明兴起的速率,各大洲不同,是生物地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