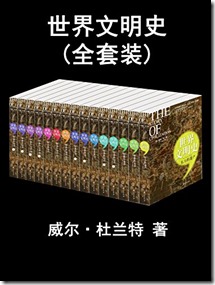《世界文明史》
这套书实在是太长了,可算是在 kindle 上读过最大部头的了,我只能说是把它大略翻过,甚至连囫囵吞枣都谈不上,anyway,还是做了一些摘录,也附在下面:
这些具有专长的部落或村落,有时是用他们所从事的工业为姓氏,如铁匠、渔人、窑匠等(Smith,Fisher,Potter……),随之,这些姓氏便成为家庭区别的依据。
罗马人使用两个很类似的词——“Pecus”和“Pecunia”来代表牛与钱,并在早期使用的钱币上印上牛的形状。我们所用的词如资本、动产(Chattel)以及牛都是源由拉丁文“Capitale”一词经法文传下来的,该词原义就是财产(Property)。“Capital”又由“Caput”一词衍化而来,原意为“头”(Head),也就是说,牛的头数。
时间认可了一切,甚至劣迹昭彰的赃物,在强盗子孙手里一变而为神圣与正当的财产。每一个国家,一开始都是强制。但这服从的习惯竟变成了良知,不久每个国民都会为忠于国家而深受感动。
因为在原始社会里,风行婚前关系,情欲不可能凭克己来杜绝,因此对妻室的选择并不造成影响。同一原因——欲望与满足之间几乎没有时距——对起伏不定的内在欲望没有时间去抑制并进而使它理想化,这种情欲的抑制正是少年期里出现的“罗曼蒂克”爱情的根源。这样的爱情迟至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才能产生,在文明的社会里,伦理的出现规范了欲望,财富的产生致使某些男人能出高价,而女人提供奢侈与优美的“罗曼蒂克”气氛。原始民族生活穷困,何来“罗曼蒂克”呢!
我们可假定数字是最早的一种书写符号,通常都是用与手相同的记号来代替数目。当我们说出数字时,都用手指脚趾来表示,故乃说是多少手指头。如“five”一词,在德文是fünf,在希腊文是Pente,回溯它的原意是代表一只手。因此罗马文里的“V”即代表张开的手掌,“X”是两个“V”联结一起。
谈到文字,我们便会联想到字母。字母可说是埃及人的一大发明。这些字母,由埃及人传给腓尼基人,由腓尼基人带到地中海,最后,由希腊罗马传遍西方。字母可算是东方人留给西方世界的最大的文化遗产。
据神话,通天塔之所以以巴别尔(Babel)命名,即含有babble说话混淆,或模糊不清之意。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据考证,Babel在巴比伦语中,乃“神的门户”之意。
犹太人最初爬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是一个终年流浪的游牧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也是见着什么都下拜,拜天、拜地、拜石头、拜山、拜洞、拜牛、拜羊。在所有崇拜事物中,犹太人特别崇拜的是公牛、羊和羊羔。埃及人也崇拜牛,犹太人住在埃及时,自然更加深了对牛的崇拜。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一再告诫犹太人勿崇拜邪神,而他们还是要崇拜“金牛”的原因。
信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观念,在犹太是慢慢形成的。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的宗教最初也是多神教。耶和华原为迦南土著民族所信神道之一,这位神,迦南人称之为雅胡(Yahu)。犹太人征服迦南后,雅胡也接受了改造,于是便成耶和华。
波斯传说,远在基督降生前数世纪,在雅利安人的故乡,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位先知就是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希腊人嫌这个名字不好念,特把他叫做琐罗亚斯德。
我们对原初印度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吠陀经》,但《吠陀经》到底是什么?“吠陀”(Veda)一字的意义是知识,是一部学问的书籍。这一经典被早期印度人民用来研究神圣的学问,正如《圣经》一样。
印度人曾经容许外邦政府一再地君临其上,部分是由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他们更看重的是宗教而非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阿育王成了圣者,阿克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甚至最强有力的人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那个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圣者。
在我们得自东方的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阿拉伯数字与十进位法,两者都是源自印度而经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阿拉伯数字最早见于阿育王的《岩石垂谕》(公元前256年),比这些数字之见于阿拉伯典籍要早上1 000年。
人生不外是伏尔泰与卢梭,孔子与老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基督,一下子趋向伏尔泰,一下子趋向卢梭,一下子趋向孔子,一下子趋向老子,一下子趋向苏格拉底,一下子趋向基督。等到每一个想法占据我们的心灵,并且不太明智或过分地为它奋斗过时,我们将倦于战斗。然后我们将和卢梭、老子耽于森林中,而与动物为友,并且比马基雅弗利更知足地以朴实的农夫心境相互交谈;令整个世界自生自灭而不费心地企求进一步的改革。
由于许多希腊思想家对于民主的庸俗和混乱感觉厌倦和恐惧,因而逃避现实,转向于对斯巴达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崇拜。 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斯巴达,所以不妨对其尽量赞颂。他们也无法感觉出自私、冷酷和残忍等斯巴达特性;他们不能就所见的精选绅士或所赞扬的远处英雄,看出斯巴达体制除产生优秀战士外一无是处;更不能体会处在斯巴达的制度下,对于事物的思考力已被抹杀,以至于仅有肉体上的强壮与残酷存留着。由于这种体制、规范和风尚的胜利,使得在它崛起之前一度兴盛的艺术文物毁于一旦。
毕氏于完成上述的数学和天文学贡献后(较欧洲任何建立科学的人贡献为多),即进而研究哲学。哲学这个字显然就是他所创造的名称之一。他拒绝使用“Sophia”(智慧)这个字,他认为这个字过于自负,他解说他那种对知识的追求为“Philosophia”——智慧的爱好。在公元前6世纪时“Philosopher”(哲学家)和Pythagorean(毕达哥拉斯学派者)是同义语。
雅典法律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开明,只是比汉谟拉比法典稍微进步。其最大的缺点是法律权利仅限于不及总人口1/7的自由人。即自由妇女与儿童也被摒弃在可骄傲的公民平等权之外。侨居雅典的人、外国人、奴隶仅能在公民的赞助下才可提出告诉。
希腊人说,自由人不应该受经济事务羁绊,他必须交由奴隶或其他人来照顾物质上的问题,如可能,甚至让他们来看管自己的财产,只有像这样的了无牵挂,他才能有时间为政府、战争、文学及哲学效力。以希腊人的观点,没有有闲阶级便没有鉴赏的标准,便不能促进艺术,更无文明。
所有这些雅典人的条件,汇集一起而创造了他们的城邦。雅典就是由他们的精神与勇气、他们的聪颖与饶舌、他们的放纵与贪婪、他们的虚荣与爱国心、他们对美与自由的崇拜,所综合创立而成。但因为他们自由,因为每一政府机关对每一公民公开,而且交替治人及受制于人,他们将一生中的半数时间贡献给国家。家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生活”在市场、议会、审议委员会、法院,以及为荣耀其城邦与神祇而举行的盛大庆典、运动竞赛及戏剧中。
希腊数学从来没有零的符号。像我们的数学显示出曾受东方人影响一样,希腊人计数所用的十进位来自埃及,而其用于天文地理之计数,则采用巴比伦的12或60进位法,今天我们的钟表、地球仪、地图仍旧沿用。
希腊城邦的弱小对个人而言,如果说在肉体方面不是个福音,至少在精神方面也必然是个福音。自由之代价虽然昂贵,却促成了希腊人在心智方面的成就。个人主义摧毁团体的同时也刺激了个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探讨以及艺术的创造。
它以宗教的神圣赋予公共生活的每一阶段,政府的每一行动皆以仪式及祈祷开始,把国家熔化于与神那么密切结合的状态中,使对神的虔敬与爱国主义打成一片,养成了狂热的爱国心,比历史上我们所知的其他社会更强烈。总而言之,宗教与家庭共同养成荣誉与责任,而形成奇特的性格,那性格就是罗马成为世界主人的秘诀。
民主制度只有在百姓都是善良的时候才算好制度,但是西塞罗认为百姓不可能永远善良。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混合政体,像格拉古兄弟以前的罗马政体:议会的民主权力,元老院的贵族权力,任期一年的执政无上权力等。缺乏制衡,君主政体就会变成专制政体,贵族政治则变成寡头政治,而民主制度也就变成暴民政治——混乱且独裁的统治。
历史也像新闻,因为它喜欢特殊。往往避开诚实人和没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或者正常的一天中,那些不被人知道的例行公事。
关于基督出生的明确日期,我们并不清楚。希腊神学家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当年(约公元200年)记录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年鉴编纂者认为基督出生在4月19日,有些说是5月20日,克莱门特本人认为是公元前3年11月17日。早在2世纪时,东方的基督教在1月6日庆祝耶稣的诞辰。公元354年,包括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教会在12月25日纪念基督的诞辰。这是当时推算错误的冬至日,冬至也就是白昼开始加长的日子。这一天原来是密特拉教(Mithraism)的主要节日,也就是所谓太阳神(密特拉教所奉的太阳神)的诞生日。东正教有一段时期坚持1月6日是耶稣诞辰,并且指责西方的教友崇拜太阳及崇拜偶像。不过到了4世纪末叶,东方教会也采用了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诞辰。
基督教并没有破坏异教,相反,它接受了异教。许多已经消失的希腊思想,均在基督教的神学或礼拜中复生。统治了哲学几个世纪的希腊语,也成为基督教文学与仪式的传达工具。许多希腊的神秘气氛,也进入了感人的弥撒仪式中。其他的异教文化也促成了基督教与各种不同文化、学说、信仰的融合。“三位一体”、“最后的审判”、永生及永远的惩罚的观念来自埃及。对圣母与圣子的崇拜及神秘的“通神论”,造成“新柏拉图主义”及“诺斯替主义”,并搅浑了基督教教条。而基督教的修道制度,也可以在埃及找到它的范例及根源。对于圣母的特别敬拜是来自弗里吉亚,阿多尼斯神复活的剧乃是出自叙利亚,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或许是来自色雷斯。“千年国度”之说、“最后的火灾”、上帝与撒旦、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这些都是出自波斯。而在《约翰福音》中也曾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密特拉教的仪式与弥撒时的圣餐仪式非常相近。
人们困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饥渴中便发轫了这个组织。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言,教会带来了足以鼓舞从容就死的信仰和希望。
教会一旦获胜之后,便不会提倡容忍;教会对信仰上之个人主义的敌视,就如同国家对于分裂或反叛的看法一样。不论是教会或异端教派,都不是以纯粹神学的眼光来看异端思想。所谓异端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所树起的思想旗帜而已。
但是如果理性不幸失败,科学不能找到答案,无力改善良心而仅使知识和权力衍生,那么这丝毫无益于人类;如果所有乌托邦残酷地因强者对弱者不变的虐待而崩溃,则人们便可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一度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的野蛮中,背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目的,而避难于谦卑的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并历时一千年之久。
文化乃是土地与心智的结合——即地上的资源,由人类的欲望和戒律衍生而成。在所谓宫廷、寺庙等宏伟建筑,在所谓文学、艺术等豪华生活的背后,都托举出这些艺术品的基本元素。如猎人创造了在森林中的各种娱乐及运动;木匠发明了伐木事业;牧人发展出畜牧事业;而农人则整理、耕植、播种,收割兰花、葡萄,养蜜蜂及照料孵雏;女人则发展各种副业,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矿工开采矿藏;匠人设计居室、车辆及船只;工匠设计各种工具及生产各种产品;贩夫、店主及商贾调和、划分制造者及消费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企业家利用储蓄发展工商业;执行者则集聚体力、财力及智力以创造服务机会并增加物资生产。这种种事业就像一只忍辱负重的巨兽,在它那摇曳负重的背脊上,文明就这样逐渐发芽、茁壮。
犹太人是以民族而非个人的立场来解释得救的。他们受到明显的无情残酷的排挤,故坚信他们是上帝特选和宠爱的民族,如此才使自己更坚强而屹立不倒。
不过,一般说来,封建欧洲的国王,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者,倒不如说是封臣的代表。他们是由大贵族和教会选举或确立的。他们直接的权力只限于自己的封建领地或庄园。在他们王国的其他地方,农奴和封臣向保护他们的领主,而很少向国王宣誓效忠,因为他微不足道且遥不可及的军事力量,无法达到并守卫其国土上散布各处的所有村落。在封建制度之下,国家只是国王的产业而已。
《大宪章》因奠定了今日英语世界享受各种自由的基础而闻名。它确实是有限制的;主要确定贵族与神职人员的权利,而非所有人民的权利;并没有任何设计以执行表示虔敬的第六十条。此宪章之签定,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胜利,毋宁说是封建制度的得势,但它明定及保障基本权利;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及陪审团审判制度;给予初期的巴力门控制钱袋的权力,以抗拒专制政治;它使专制的君主政体转变为立宪的君主政体。
他(达·芬奇)只写了简单的遗嘱,但于其葬礼上却要求全部的宗教仪式。他曾写道:“一日操劳,睡得安逸;一生尽责,死亦无憾。”
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基督徒、犹太人与回教徒,比我们今日更敏锐地关怀宗教一事。他们的神学理论,乃是他们的至宝与信托品。他们将拒斥这些信条的人士,视为攻击社会秩序基础及人类生命真正意义的敌人。每一集团均因确信而难以容忍,并将他人视为异端。
奥卡姆挟着摧毁性的鲁莽,而从这一“唯名论”闯入哲学、神学的每一领域。形而上学与科学,他宣称道,都是过早的普遍化,因为我们的经验只是属于狭窄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的个别实体;我们若将我们从实际存在界中的这一渺小区落里所获得的一般命题与“自然法则”,直称为普遍并永恒真实,就我们而言,这只是我们的高傲而已。我们的知识乃受到我们观测事物的方法与方式所塑造、所限制,这是康德(Kant)之前的康德。它被锁在我们心灵的监狱里,绝不能伪装为任何事物的客观或终极真理。
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将印刷品利用作为宣传和争论工具的人。当时并无报纸,也没有杂志,争论全靠书本、小册子和有意公开的私人信件。由于马丁·路德的刺激,日耳曼印刷的书本数量,从1518年的150本,提高到1524年的990本,其中4/5是有关宗教革命的书籍。支持罗马教会的书籍很难出售,而马丁·路德的书籍,却是当时最抢手的书籍,不仅书店经销,连小贩和学生都在出售。仅爱尔福特市集一处,就卖掉1 400本。在巴黎,1520年时,其销售量甚至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早在1519年,他的书籍就已经外销至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即荷兰)、英格兰等地。伊拉斯谟于1521年写道:“马丁·路德的书籍流传到各处,而且有各种语言的版本。没有人敢相信,他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广泛。”宗教改革家的文学创作力,把占优势的作品,从南欧传到北欧,一直维持到现在。印刷品就是宗教改革。左腾贝格(日耳曼活字印刷发明人)促使马丁·路德成功。
有一些天文学家看到哥白尼这篇小评并没有加以太多的注意。教皇利奥十世亦知道此一理论,并表示他非常有兴趣,故叫一红衣主教写封信给哥白尼,要他示范证明其假说。当时,这种学说在开明的教皇宫廷内确实受到相当的好评。一直到了1530年路德才拒绝此种理论:“人们信服那个极欲展示地球在周转而不是苍天或太阳及月亮在转的暴发户占星家……这个愚人希望改变整个天文的体系,但《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屹立不动,而不是地球。”加尔文引用圣诗第1003章(Psalm XCIII)的话回答哥白尼说:“这个世界也是固定的,它不能移动。”他并且反问:“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
“这个世界对于能思想的人是个喜剧,对于富有感情的人是个悲剧”
很显然,历史的编纂不能算是一种科学。它只能算是一种工业、一种艺术以及一种哲学——搜集史实即工业,在混乱的资料中建立具有意义的系统即艺术,寻求透视与启迪作用则是哲学。